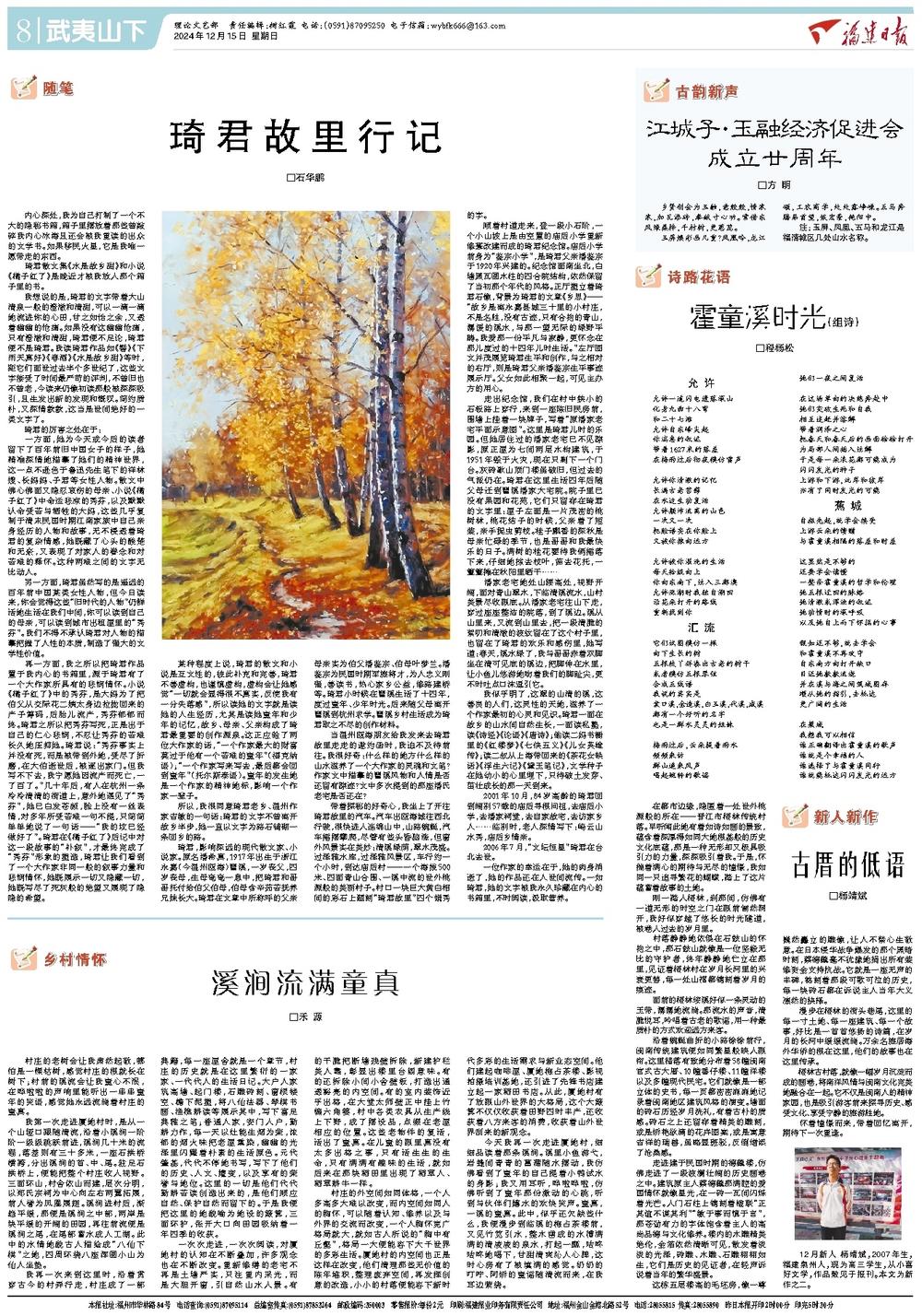内心深处,我为自己打制了一个不大的隐秘书箱,箱子里摆放着那些曾敲碎我内心冰海且还会被我重读的出众的文学书。如果移民火星,它是我唯一愿带走的东西。
琦君散文集《水是故乡甜》和小说《橘子红了》是晚近才被我放入那个箱子里的书。
我想说的是,琦君的文字带着大山清泉一般的澄澈和清甜,可以一滴一滴地流进你的心田,甘之如饴之余,又透着幽幽的怆痛。如果没有这幽幽怆痛,只有澄澈和清甜,琦君便不足论,琦君便不是琦君。我读琦君作品如《髻》《下雨天真好》《春酒》《水是故乡甜》等时,距它们面世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些文字接受了时间最严苛的评判,不曾旧也不曾老,今读来仍像初读那般被深深吸引,且生发出新的发现和慨叹。简约质朴,又深情款款,这当是世间绝好的一类文字了。
琦君的厉害之处在于:
一方面,她为今天或今后的读者留下了百年前旧中国女子的样子,她精准深情地描摹了她们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不逊色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长妈妈、子君等女性人物。散文中佛心佛面又隐忍哀伤的母亲、小说《橘子红了》中命运悲凉的秀芬,以及默默认命受苦与牺牲的大妈,这些几乎复制于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家族中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物和故事,无不浸透着琦君的复杂情感,她既藏了心头的酸楚和无奈,又表现了对家人的眷念和对苦难的释怀。这种两难之间的文字无比动人。
另一方面,琦君虽然写的是遥远的百年前中国某类女性人物,但今日读来,你会觉得这些“旧时代的人物”仍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你可以读到自己的母亲,可以读到城市出租屋里的“秀芬”。我们不得不承认琦君对人物的描摹把握了人性的本质,制造了强大的文学性价值。
再一方面,我之所以把琦君作品置于我内心的书箱里,源于琦君有了一个大作家所具有的悲悯情怀。小说《橘子红了》中的秀芬,是大妈为了把伯父从交际花二姨太身边拉拢回来的产子筹码,后胎儿流产,秀芬郁郁而终。琦君之所以把秀芬写死,正是出于自己的仁心悲悯,不忍让秀芬的苦难长久地压抑她。琦君说:“秀芬事实上并没有死,而是被带到外地,受尽了折磨,在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门。但我写不下去,我宁愿她因流产而死亡,一了百了。”几十年后,有人在杭州一条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意外地遇见了“秀芬”,她已白发苍颜,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对多年所受苦难一句不提,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坟已经做好了”。琦君在《橘子红了》后记中对这一段故事的“补叙”,才最终完成了“秀芬”形象的塑造,琦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作家非同一般的叙事力量和悲悯情怀,她既展示一切又隐藏一切,她既写尽了死灰般的绝望又展现了隐隐的希望。
某种程度上说,琦君的散文和小说是互文性的,彼此补充和完善,琦君不善虚构,也谨慎虚构,虚构会让她感觉“一切就会显得很不真实,反使我有一分失落感”,所以读她的文字就是读她的人生经历,尤其是读她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故乡、母亲、父亲构成了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源泉。这正应验了两位大作家的话,“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福克纳语);“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托尔斯泰语)。童年的发生地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地标,影响一个作家一辈子。
所以,我很同意琦君老乡、温州作家吉敏的一句话:琦君的文字不曾离开故乡半步,她一直以文字为路石铺砌一条回乡的路。
琦君,影响深远的现代散文家、小说家。原名潘希真,1917年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瓯海)瞿溪,一岁丧父,四岁丧母,生母奄奄一息中,把琦君和哥哥托付给伯父伯母,伯母含辛茹苦抚养兄妹长大。琦君在文章中所称呼的父亲母亲实为伯父潘鉴宗、伯母叶梦兰。潘鉴宗为民国时期军旅将才,为人忠义刚强,善读书,热心家乡公益,修路建桥等。琦君小时候在瞿溪生活了十四年,度过童年、少年时光。后来随父母离开瞿溪到杭州求学。瞿溪乡村生活成为琦君取之不尽的创作材料。
当温州瓯海朋友给我发来去琦君故里走走的邀约函时,我迫不及待前往。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山水滋养了一个大作家的灵魂和文笔?作家文中描摹的瞿溪风物和人情是否还留有踪迹?文中多次提到的那座潘氏老宅是否还在?
带着探秘的好奇心,我坐上了开往琦君故里的汽车。汽车出瓯海城往西北行驶,很快进入连绵山中,山路蜿蜒,汽车摇摆攀爬,尽管有些头昏脑涨,但窗外风景实在美妙:清溪绿荫,翠木茂盛。过泽雅水库,过泽雅风景区,车行约一个小时,到达庙后村——一个海拔500米、四面青山合围、一溪中流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丽村子。村口一块巨大黄白相间的彩石上题刻“琦君故里”四个娟秀的字。
顺着村道走来,登一段小石阶,一个小山坡上是由空置的庙后小学重新修葺改建而成的琦君纪念馆。庙后小学前身为“鉴宗小学”,是琦君父亲潘鉴宗于1920年兴建的。纪念馆面南坐北,白墙黑瓦圆木柱的四合院结构,依然保留了当初那个年代的风格。正厅塑立着琦君石像,背景为琦君的文章《乡思》——“故乡是离永嘉县城三十里的小村庄,不是名胜,没有古迹,只有合抱的青山,潺湲的溪水,与那一望无际的绿野平畴。我爱那一份平凡与寂静,更怀念在那儿度过的十四年儿时生活。”左厅图文并茂展览琦君生平和创作,与之相对的右厅,则是琦君父亲潘鉴宗生平事迹展示厅。父女如此相聚一起,可见主办方的用心。
走出纪念馆,我们在村中狭小的石板路上穿行,来到一座陈旧民房前,围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原潘家老宅平面示意图”。这里是琦君儿时的乐园。但她居住过的潘家老宅已不见踪影,原正屋为七间两层木构建筑,于1951年毁于火灾,现在只剩下一个门台。灰砖歇山顶门楼虽破旧,但过去的气派仍在。琦君在这里生活四年后随父母迁到瞿溪潘家大宅院。院子里已没有果园和花苑,它们只留存在琦君的文字里:屋子左面是一片茂密的桃树林,桃花结子的时候,父亲着了短装,亲手捉虫剪枝。桂子飘香的深秋是母亲忙碌的季节,也是哥哥和我最快乐的日子。满树的桂花要待我俩摇落下来,仔细地拣去枝叶,筛去花托,一簟簟摊在秋阳里晒干……
潘家老宅地处山腰高处,视野开阔,面对青山翠木,下临清溪流水,山村美景尽收眼底。从潘家老宅往山下走,穿过座座整洁的院落,到了溪边。溪从山里来,又流到山里去,把一段清脆的絮叨和清澈的波纹留在了这个村子里,也留在了琦君的欢乐和感伤里,她写道:春天,溪水绿了,我与哥哥赤着双脚坐在清可见底的溪边,把脚伸在水里,让小鱼儿悠游地吻着我们的脚趾尖,更不时吐点口沫逗引它。
我似乎明了,这翠的山清的溪,这善良的人们,这灵性的天地,滋养了一个作家最初的心灵和见识。琦君一面在故乡的山水间自然生长,一面读私塾,读《诗经》《论语》《唐诗》;偷读二妈书橱里的《红楼梦》《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读二叔从上海带回来的《茶花女轶话》《浮生六记》《黛玉笔记》,文学种子在她幼小的心里埋下,只待破土发芽、茁壮成长的那一天到来。
2001年10月,84岁高龄的琦君回到阔别57载的庙后寻根问祖,去庙后小学,去潘家祠堂,去自家故宅,去访家乡人……临别时,老人深情写下:崎云山水秀,庙后乡情亲。
2006年7月,“文坛恒星”琦君在台北去世。
一位作家的幸运在于,她的肉身消逝了,她的作品还在人世间流传。一如琦君,她的文字被我永久珍藏在内心的书箱里,不时阅读,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