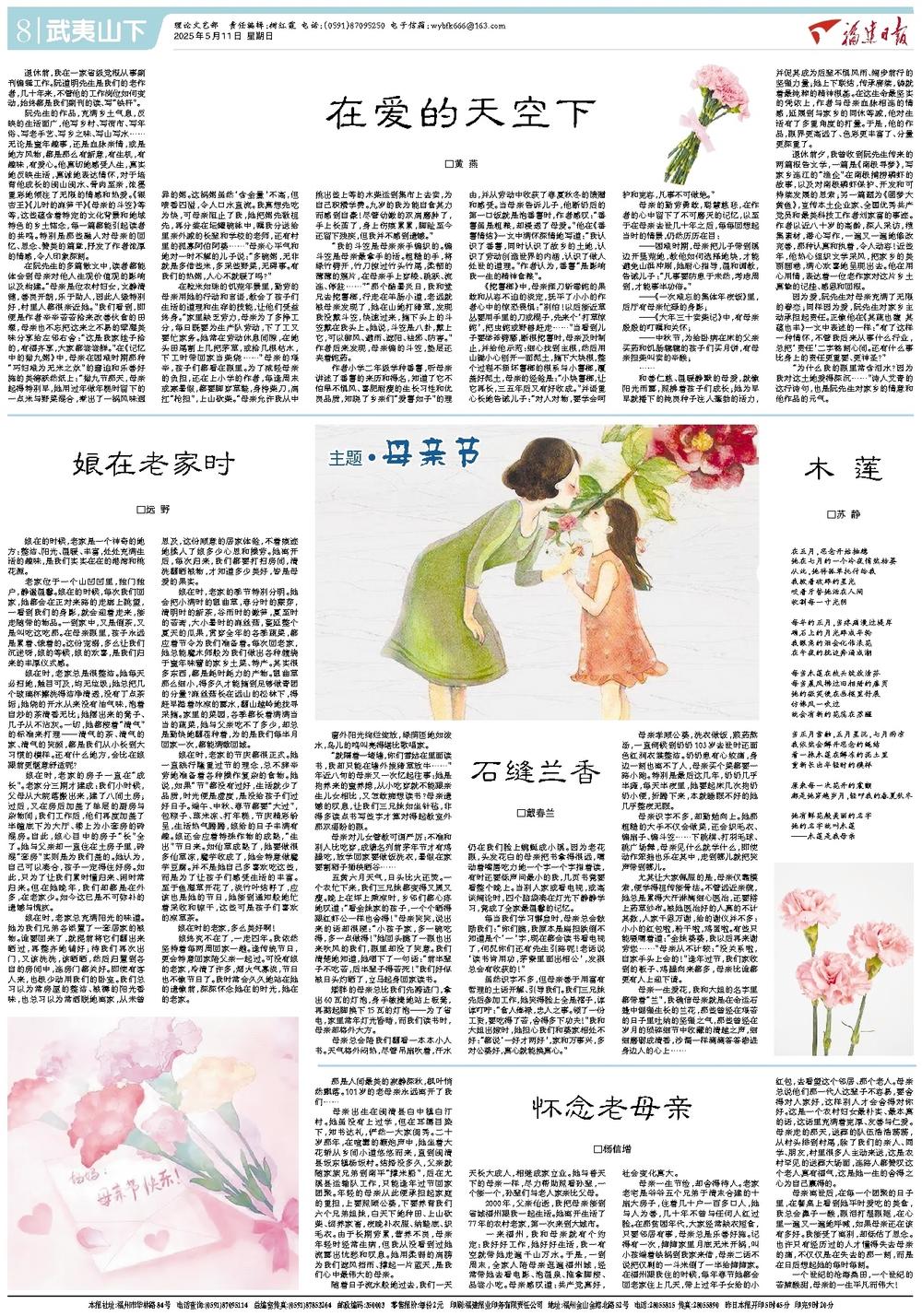窗外阳光绚烂绽放,绿荫匝地如泼水,鸟儿的鸣叫亮得堪比歌唱家。
“就隔着一堵墙,你们雪姑在里面读书,我却只能在墙外拔猪草放牛……”年近八旬的母亲又一次忆起往事:她是抱养来的童养媳,从小吃穿就不能跟亲生儿女相比,又怎敢痴想读书?母亲遗憾的叹息,让我们三兄妹如坐针毡,非得多读点书写些字才算对得起教室外那双渴盼的眼。
母亲对儿女管教可谓严厉:不准和别人比吃穿,成绩名列前茅年节才有鸡腿吃,放学回家要做饭洗衣,暑假在家要割稻子插秧晒谷……
五黄六月天气,日头比火还烫。一个农忙下来,我们三兄妹都变得又黑又瘦。晚上在坪上乘凉时,乡邻们都心疼地叹道:“看金妹家的孩子,一个个晒得跟红虾公一样也舍得!”母亲笑笑,说出来的话却很硬:“小孩子家,多一碗吃得,多一点做得!”她回头瞧了一眼也出来吹风的我们,眼里却没了笑意。我们清楚地知道,她咽下了一句话:“前半辈子不吃苦,后半辈子得苦死!”我们好似被日头灼晒了,立马起身回家读书。
矮胖的母亲总比我们先跨进门,拿出60瓦的灯泡,身手敏捷地站上板凳,再踮起脚换下15瓦的灯泡——为了省电,家里常年灯光昏暗,而我们读书时,母亲却格外大方。
母亲总会陪我们翻看一本本小人书。天气格外闷热,尽管吊扇吹着,汗水仍在我们脸上蜿蜒成小溪。因为老花眼,头发花白的母亲把书拿得很远,嚅动着嘴唇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读,有时还要低声问最小的我,几页书竟要看整个晚上。当别人家或看电视,或高谈阔论时,四个脑袋凑在灯光下静静学习,竟成了全家最温馨的记忆。
每当我们学习懈怠时,母亲总会鼓励我们:“你们瞧,我原本是扁担跌倒不知道是个‘一’字,现在都会读书看电视了,何况你们还有先生引路呢!老话说‘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发狠总会有收获的!”
虽然识字不多,但母亲善于用富有哲理的土话开解、引导我们。我们三兄妹先后参加工作,她笑得脸上全是褶子,谆谆叮咛:“食人俸禄,忠人之事。领了一份工资,要吃得了苦,舍得多下功夫!”我和大姐出嫁时,她担心我们和婆家相处不好:“都说‘一好才两好’,家和万事兴,多对公婆好,真心就能换真心。”
母亲孝顺公婆,洗衣做饭,煎药熬汤,一直伺候到奶奶103岁去世时还面色红润衣裳整洁。奶奶患有心绞痛,身边一刻也离不了人,母亲买个菜都要一路小跑。特别是最后这几年,奶奶几乎半瘫,每天半夜里,她要起床几次抱奶奶小便,折腾下来,本就睡眠不好的她几乎整夜无眠。
母亲识字不多,却勤勉向上。她那粗糙的大手不仅会做菜,还会织毛衣、编扇子、编斗笠……下跳棋、打羽毛球、跳广场舞,母亲见什么就学什么,即使动作笨拙也乐在其中,走到哪儿就把笑声带到哪儿。
尤其让大家佩服的是,母亲仅靠摸索,便学得祖传接骨法。不管远近亲疏,她总是累得大汗淋漓细心医治,还要搭上药草纱布。被她医治好的人真的不计其数,人家千恩万谢,给的谢仪并不多:小小的红包啦,粉干啦,鸡蛋啦。有些只能嗫嚅着道:“金妹婆婆,我以后再来谢劳您……”母亲从不计较:“没关系啦,自家手头上会的!”逢年过节,我们家收到的粄子、鸡腿向来都多,母亲比谁都更有人上迎下请。
母亲一生爱花,我和大姐的名字里都带着“兰”,我确信母亲就是在命运石缝中倔强生长的兰花,那些曾经在艰苦的日子里吐纳的坚强之气,那些曾经在岁月的琐碎细节中收藏的清越之声,细细磨砺成清香,沙漏一样滴滴答答渗进身边人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