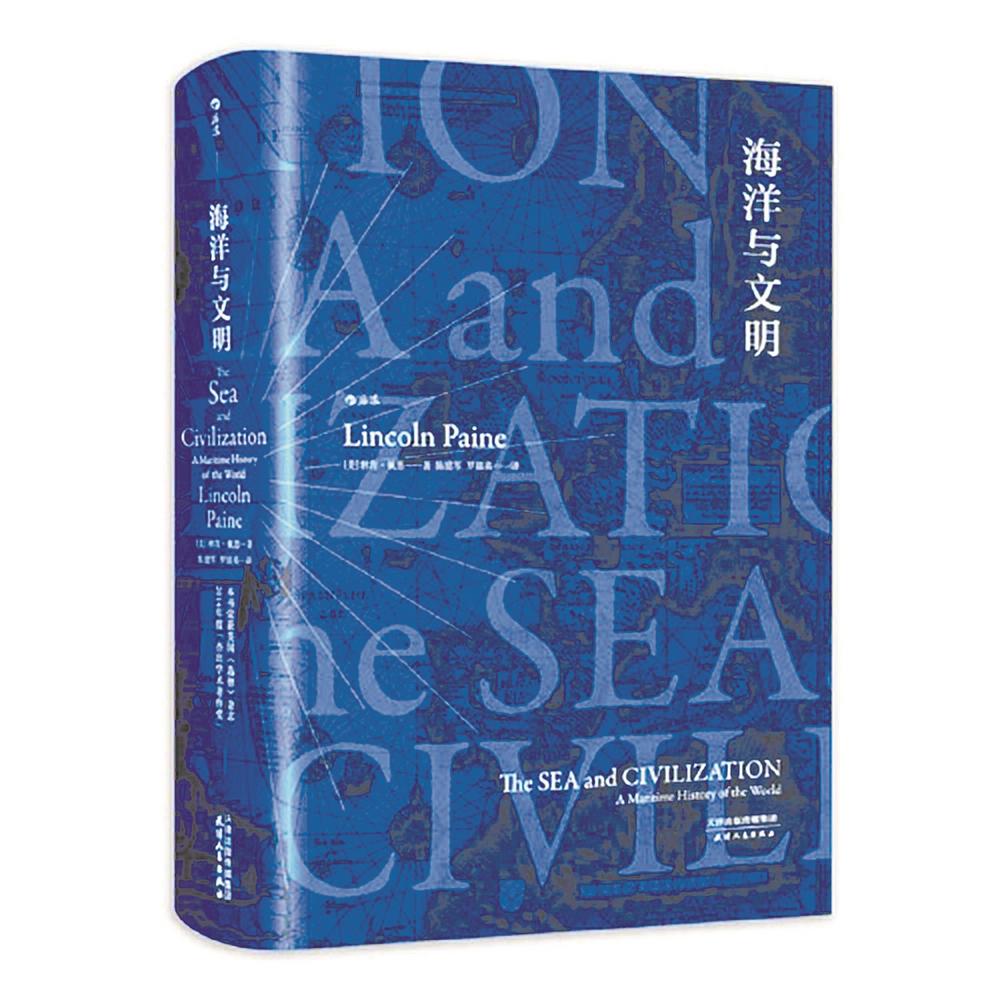长久以来,“农耕文明”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核心标签,常被用来对比“海洋文明”“草原文明”。更有甚者,将中国近代的落后与挨打归因于“农耕文明”的基因,以为靠时令耕作的民族缺乏开拓精神,而欧美列强的崛起则得益于“海洋文明”的冒险与扩张。这种二元划分,既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也遮蔽了真实的文明演进图景。
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的《海洋与文明》正是一部通过讲述人类在海洋中的活动历史来帮助人们转换思考方式的作品。他在序言中直指,中国被排除出“海洋文明”的说法根源在“欧洲中心论”,西方史学家用它来解释“现存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在19—20世纪,强大的国家拥有海权,而它们就被解释成了“海洋文明”,但这一叙事将中国长期以来在海洋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完全无视了。
所谓“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立,其实只是粗暴的贴标签行为。我们不应执着于争论我们是否具有“海洋文明的基因”,而应改变“将陆地视为家园,将海洋视为征途”的思考方式。从历史上看,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都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
佩恩之论反映了近来历史学重视陆海联动的研究视角,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明交流史新发现密切联系。从考古证据看,中原、腹地不乏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比如,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妇好墓、陕西周原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地,考古学者先后发现大量海贝遗物,尤其是“货贝”(俗称黄宝螺),这种海贝主要分布于台湾、海南等热带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印度洋-太平洋海域。这些远道而来的海贝,显然不是偶然漂流而至,而是古人通过有组织的贸易、交换,甚至迁徙传播至内陆。这说明,中国古人对海洋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与利用,从物证层面揭示出中原与东南亚、南亚、西南地区的交通路线与文化交流。
文献层面同样不乏对海洋的想象与反思。《山海经》记载大量与大海相关的神话地理,《论语·公冶长》中孔子曾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海洋从未被完全排除在中国古人视野之外。
反之,将近代欧洲强国的兴起简化为“海洋文明”的胜利,也是对历史的误读。首先,欧洲的“诞生”并不源于爱琴海的希腊,而是公元9世纪由法兰克王查理曼缔造的加洛林王朝。这个塑造欧洲雏形的政权,其疆域并不包括希腊,也并非以海洋贸易见长。
事实上,11世纪之前的西欧自身处于农耕社会的重建阶段。正是因为农业革命,包括重犁技术、挽具革新、三田轮作制的推广,西欧才得以恢复人口与经济,为日后崛起奠定基础。而此时的中国(北宋时期),海洋贸易早已繁盛,泉州、明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东亚,甚至波斯湾地区,远比当时的西欧要先进得多。
所谓“封建制度”,无论在中世纪欧洲,还是在中国,其核心都是围绕土地。领主通过分封土地建立统治关系,而不是围绕海洋。这一事实说明,重视土地,并非“农耕基因”的束缚,而是当时所有文明的共同选择。
真正应当反思的,并不是我们是否属于“农耕文明”,而是我们曾否主动放弃过海洋。明清之际,“惧海”的心理逐渐占上风,海风之凶、海寇之害、列强之逼,使得统治者闭上眼睛、关上国门,丧失了原本属于我们的海洋机遇。
《海洋与文明》这部近70万字的巨著,以时间为经、航线为纬,从史前时代至21世纪,穿越全球七大洋,以一种宏阔的视野重新描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
不同于以往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史叙述方式,佩恩将“海洋”置于人类历史的核心。他不仅关注海上帝国的兴衰、商贸网络的构建、航海技术的演进,更重视海洋对文化、宗教、语言、疾病传播乃至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对中国古代海洋活动的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价。佩恩打破了西方历史书写中惯有的“东方缺席”视角。他沿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进行考察,从汉代南方海上贸易的开辟、宋元港口贸易的繁荣,到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国始终是全球海洋秩序的重要参与者。
佩恩也并未回避明清时期“弃海”策略所带来的后果。他指出,中国曾主动构建过全球最为庞大的海上外交与贸易体系,却在政策层面逐步收缩,最终将海洋空间拱手让人。这一判断,呼应了今日中国重新“走向深蓝”的历史背景,使读者得以在全球史中理解当前的“海洋战略”。
更重要的是,佩恩并非单纯讲述“谁更早航海”“谁发现了新大陆”,他追求的是“航行中的文明史”视角。让我们看到,海洋是人类迁徙、交流、融合与冲突的重要舞台。这样的视角,恰恰可以打破固有的地缘思维,为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层的思想资源。